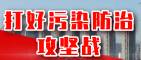本文為《晉劇坤伶須生開宗泰斗丁果仙》之《品評》卷序三,由北岳文藝出版社授權發布
此時此刻,當我臨紙揮毫,為給近代晉劇史上開宗立派、獨領風騷多半個世紀的曠代碩果丁果仙立傳的三卷本作序時,我的心情,可謂是興奮至極,欣慰至極,又惶愧至極!何以故?說來話長,但又必須從頭概述緣由——
1961年,我由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山西。荷蒙時任省戲研室主任易風王老的垂青,不棄我右傾分子之身份,錄用我在其麾下從事劇評與表演藝術研究。于是,我這個生長于長江東海之濱的“南人”,便有幸與山河襟帶的黃土高原之上的北國“亂彈”——以晉劇為主的梆子腔地方戲曲結下了不期而遇的十年緣分。易老(王易風)與丁大師便是我傾心于晉劇的兩位系紅繩的“月老”。如果說,我在省戲研室見習的頭年是出于對易老知遇圖報之情而硬著頭皮出入戲院投入晉劇懷抱的話,那么,次年亦即1962年的晉劇院青年團赴京返并的匯報演出,尤其是當年7月隆重舉辦的丁果仙舞臺生活四十年的紀念演出,則是我興味盎然接受晉劇藝術熏陶、心旌搖蕩領略晉劇風騷的初始發軔。青年團赴京載譽歸來演出的打磨多年的《打金枝》《小宴》《殺宮》《算糧》等精品傳統劇,令我耳目一新地感受到傳承與創新完美結合的那種當代戲曲表演藝術的情韻,一味高亢火爆鼓板震耳數里聞唱的鄉野班社的氛圍已適度淡化;欣賞了丁果仙和她的高足們連續數日的丁派經典劇目的震撼上演,聆聽寒聲、易老等專家的精彩講評,翻閱了手頭可尋的文字資料,我認識到丁大師原本是將近代晉劇的表演藝術做了去粗存精改造與唱、做、念、白兼佳的創新,從而成為獨領舞臺風騷的晉劇現代化表演藝術的奠基人之一。懷著對她的高度崇敬,年輕好強的我馬上開始動筆,于當年9月在《戲劇報》發了由我執筆的《談丁果仙演〈八件衣〉中的楊知縣》一篇六千字的評論文章,之后,我便不測深淺地暗自將系統研究丁氏表演藝術作為自己的主攻課題。或許是心有靈犀不點自通的緣故吧,識見不凡、用人有方的易老便給我和與我同室而居的、也是經易老當年調入省戲研室的、由吉林大學歷史系畢業的艾治國君委派了編寫《丁果仙舞臺生活四十年》專著的重任。在易老的親自策劃安排下,我倆歷時半載,如同門私淑弟子一般在大師府上接受大師口傳身教的授業,又歷半年許,我倆按許姬傳所著《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的基本格局,以第三人稱口吻將丁氏口述身授的記錄文字,分“藝術生平”與“代表作藝談”兩大篇章,加工整理,成形為初稿。據易老告知,中國戲劇出版社派來專人翻閱了已成形的初稿,簽訂了出版意向書。正當我們摩拳擦掌慎始慎終,力爭一鼓作氣圓滿完成編寫任務時,世事風云劇變,愈演愈烈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教運動與史無前例的“文革”接踵而至,災連禍接延續十多年,先后將我們卷入洶涌大潮。待到幸免于滅頂之災后,雖可再舞文墨,但物固不是,人亦全非,舊業難操。“文革”初期,“丁傳”文稿先是被入室打砸搶的造反“好漢”洗劫而去,下落不明;繼之是傳主丁果仙被整被斗病骨支離含冤飲泣過早辭世;再繼之是“文革”后期,我等先是下放后是錯位回歸,各自另展宏圖。我由山野村夫搖身成為編書匠。改革開放初期,一頭扎進我所創辦的《名作欣賞》雜志的編事冗務中,不遑他顧;但稍有閑暇,依然魂牽夢繞丁大師,深感不在她的墳墓上奉獻一瓣心香,實是有愧她的厚愛,有負她的厚望。于是,在她逝世十周年前后,利用零星的業余時間,挖掘記憶殘存,雜拾報刊前已發表可資翻新的文墨,陸續在省內報刊上發表了一組《丁果仙藝術生涯談片》的短文。大約在她逝世二十周年時,受原戲劇界同仁的敦促,應山西《戲友》雜志所約,勉為其難,化零為整,敷演鋪陳為不足四萬字的《丁果仙藝術生涯評傳》專文,連載刊發,后經充實修訂,于2006年納入《山西歷史文化叢書》第二十輯。2009年為紀念丁氏百年誕辰編印《晉韻流芳》一書時,拙著仍為篇幅最長傳評相兼的專文忝列其中。
從1992年始,至2010年以后,拙著跨兩個世紀,逾二十多年,以瘦骨伶仃、老態龍鐘之相,支應了數次丁氏紀念性的學術研討會,實屬一大尷尬。特別是偶聽外來與會專家謬贊拙著為丁氏身后唯一留存的遺響絕唱時,我這尚有自知之明的作者,真如芒刺在背,汗顏淋漓,無地自容。捫心自問,愧對丁氏有三:一,“文革”前,為在“四清”運動中有出色的表現,幾乎將“丁傳”的出版置諸腦后,未在“四清”運動每期參與的間隙中,發力沖刺出書;二,“文革”伊始,謀于自保,陷入派爭,疏于妥存丁傳文稿與原始記錄,致使輕易丟失于集體宿舍中;三,改革開放后,改行作嫁,不惑之年,忙于在新領域中奮進求成,雖因陋就簡,寫成評傳,但未抽暇及時廣為走訪,搜羅第一手資料,大幅度修訂評傳,使其厚重豐滿,庶幾可與丁氏的藝術成就相匹配。待到退居林下后,雖閑暇多有,但年老體弱,居無定址,不克再操舊業,只愛落拓江湖,游山玩水,行吟自怡。丁氏評傳的“修葺”乃至“重建”,雖不時縈懷,但心有余力不足,便一再蹉跎延擱。五年前,有自費走遍北國,甚至跨海赴臺,追蹤破解丁氏身世之謎的老戲迷段興旺君,身背一大書包的相關攝影圖文資料,訪余于寒舍,征詢出版丁氏圖傳的意見。余為其志趣情操所動,熱忱接待,傾心相告鄙見,并鼎力推崇他與我的同行同仁同事多年的華敏君合作。后華敏見告:她已加盟由老戲迷、工人作家張桂根倡議,并與太原市戲劇界原老領導楊秋實共同牽頭,太原市老劇作家趙威龍、省戲研所原副所長閻玉庭、市實驗晉劇團劉惠蘭自發組成的草根編創組,組員平均年齡已是七十有余,后段興旺也加入其中。他們決定爭取在三四年內編寫出一部紀實完善的、有文學性的丁果仙詳傳和一部珍貴影像與精煉文字璧合的丁果仙圖傳以及一部丁果仙表演藝術品評精選集,三本一套,名《晉劇坤伶須生開宗泰斗丁果仙》。
他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壯懷壯舉,深深感奮了我這個疏懶老漢的進取心。他們功德無量的作為,實際是代償了我對丁大師的歉疚,圓了我多年的夙愿。我這個丁師簡陋評傳的始作俑者,雖不能重新入伍成為寫新傳組合中的一員,但絕不能坐等拋磚所引之玉從昆侖蹦出,而必須為其大作的催生竭盡綿薄之力。于是,在乙未年初春,我耗時月余逐字逐句拜讀了趙威龍先生主筆的四十余萬字的丁傳(即《春秋》卷)初稿,并循老編輯的慣習,邊讀邊校改全文,并不計當否,逐一將褒貶的一己之見和盤托出,以資斟酌。先睹為快的總體感受是:一部當今最完備最翔實的丁果仙傳記,經諸君數年毫不懈怠的耕耘培育,終于枝繁葉茂,可望臨風招展于三晉劇壇之上。繼之,在秋后至歲末,又陸續閱讀了由華敏君執筆編寫的十余萬字的丁氏圖傳(即《影行》卷)文稿、閻玉庭和華敏執編事的丁氏評論精選精編集(即《品評》卷)的選目與編輯方案。在對此三卷本的整體面目有了不算粗略的了解,對作品五年懷胎一朝分娩的艱辛與暢懷有了感同身受的切膚體驗,方懷著上文開白所坦言的那種興奮與惶愧、欣慰與贊嘆交織雜陳的心情,不揣簡陋,絮絮叨叨地做此序文。
關于這部作品的問世,從編創組七位摯愛三晉戲曲、崇敬丁氏德藝的老戲人、老戲迷滿腔激情貢獻余熱的自發組合,到千里跋涉奔波、揭謎求真、破偽求證、拾遺求全的廣采博取的資料搜集,到不舍晝夜、魂牽夢繞、苦思冥想、群策群力的謀劃構架、設計藍圖,再到分工有序、各盡所能、通力合作、反復修改的執筆成書……凡此種種,只要稍有搦管舞文經歷的人,對個中的艱辛勞累,寢食不安的煩愁是不難有深切體味的,何況,他們的主腦主筆人均為垂老之人;更何況,兩位執筆操翰者趙威龍先生與華敏女士,當其時也,一位正遭喪妻之痛,一位獨身寡居還得侍奉久病在床年逾九秩的高堂老母,若無丁果仙人格魅力的歷久彌堅的感召、藝術光華永世不滅的輝耀、至偉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文精神的鼓舞和編創組全體成員對傳承這種精神文明的歷史使命的自覺擔當,此套書的編寫是絕不會如此順當。
丁果仙的橫空出世、輝耀藝壇,說到底,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奉天承運”、時勢使然、地靈所鐘、人望所歸;絕非仗權貴頤使、騷客吹捧、自我膨脹所能如恒岳般亙立于三晉大地的。
草根編創組富有傳奇性的編創生涯,如同傳主丁果仙的藝術生涯,令人堅信清代杰出詩論家趙翼所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是對中華五千年文明傳承的正確斷言。只不過文明史的演進車輪是與時俱進加快轉動的,而今而后,獨領風騷未必會有數百年之久。但獨領風騷的歷史人物在丹青史冊中終會名垂千秋的。
關于這套鴻篇巨制的諸多特色優長與其面世后將在省內外梨園界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先我作序的山西省文化廳原廳長曲潤海校友、原副廳長郭士星文友均高屋建瓴、言簡意賅地給予了充分的贊譽評價。他們二位均屬職司戲劇教化多年的專家學者型的領導,二位切中肯綮的評價,我深表贊同,毋庸贅為置喙。現僅對我視之為三卷合一的丁果仙“大傳”的編創設計的匠心略陳管見一二。
毫無疑問,現定名為《春秋》卷之丁果仙主傳是三卷書的主干。此著嚴格以時間為序,將丁氏自1909年降世后的現已揭破謎團的苦難身世,學藝練藝從藝的艱苦卓絕的奮進,由勇登晉中城鄉的闖關打擂式的臺口競技演出中脫穎成名,成名后的不懈奮進而譽滿省內外的巔峰攀越;及至抗戰內戰中的自保求存領班求活的顛撲困頓;直至解放后重見天日的掀髯放歌,縱情獻藝;最終在“文革”浩劫中在劫難逃不幸早逝等一連串時近一個花甲子的風生水起波翻浪涌的人生旅程與演藝生涯,無不以傳記文學的妙筆,真實生動、形象鮮明地記述描摹刻畫下來。丁果仙這位近代晉劇史上第一個應運而生的坤伶須生大王,第一個德藝雙馨、唱做雙絕的藝壇泰斗,第一個開宗立派、桃李芳菲的梨園巨擘,其傳奇人生光輝業績,其喜怒哀樂七情六欲,其舉手投足音容笑貌,幾乎都可從作者大關節目不失真確、人事細節合情虛擬的既親切樸實且富鄉土草根氣息的出色敘寫中呼之即出。運筆的生動、真切、細膩,非我等一味在書本中討生活的墨客所能為也。尤為可貴的是編創組里幾位老作者,對丁果仙時代前后的世事變遷及山西的歷史風云、社會生活、風土民情無不了然在胸,尤其對丁氏演藝活動當時的名優藝事、班社始末、梨園史話、曲壇掌故更是厚貯胸臆,一觸靈府,便難自已,隨筆展示。資料之豐厚,運筆之精細,可謂前所未見,視其為民國以降的晉劇名優之“錄鬼簿”、晉劇班社之“梨園譜”、晉劇發展之“斷代史”亦未嘗不可。但是,由于該傳涉筆的文化層面過廣,枝葉長勢過茂,在某種程度上消減沖淡了丁氏主傳的主腦主旨;另一方面,傳記的運筆,長于描述,疏于綜合論析,因此,對丁氏藝術整體之理性評價略顯薄弱。對此瑕不掩瑜的缺憾,編創組亦有所察覺并早有預案安排,加以彌補。在主傳基本形成后,立即著手編寫了《影行》卷、編選了《品評》卷,此兩書作為主傳《春秋》卷的兩翼,同時付梓推出。《影行》卷由戲曲創作和編輯工作都有佳績的華敏女士為編寫之執牛耳者。《影行》卷取影隨人行之意,將丁氏的生平與藝術人生行狀集納分類為四個層面或曰四個專題,以主傳為據,采戲即人生、人生為戲之意,匠心獨具,用戲曲體式分幕分場,幕前用諸宮調曲詞啟幕,幕落以下場對子作結,且以情韻不俗、文質相兼的筆調寫出每幕每場連貫性的簡約文字說明,相關的珍貴照片配置在相應的文字結點,作為直觀可視的行文佐證。其中“芬華藝苑”一幕為重頭戲,共分四場,占全書場次的十分之四,成為丁氏藝術生涯的集中凸現,匹配的舞臺劇照,既多且珍貴,圖文并茂地具現了丁氏的藝術人生與演藝成就。此卷庶可作為《春秋》卷的精練濃縮版讀之。同樣,《品評》卷,亦以主傳提供的素材為據,主旨明確地精選了歷來評論、品味、鑒賞、追憶丁氏的高尚人品、高超演技、卓越成就、寶貴遺產的有一定存留價值的文章,有識見地將舊文分類編排,有分寸地將同類文章中的可取處剪裁集納,有針對性地另組新作拾遺補闕,如此這般,此本《品評》卷便以客觀的具有歷史性的諸人諸種的紛紜品評取代了編創者的饒舌,成為丁氏晉韻流芳的文墨豐碑,矗立于《春秋》卷主傳的另一側與其交相輝映。此三卷本《晉劇坤伶須生開宗泰斗丁果仙》,其規模之大,其內涵之豐,其現實與歷史意義之深遠真可謂光前裕后的當前藝苑罕見的大制作。編創者們的壯志壯舉昭示三晉戲劇的同仁:只要俺們不甘坐視三晉劇壇的式微,只要俺們能如七老一樣同心同德迎難而上,山西戲曲大省的昔日輝煌,或可重現于俺們的有生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