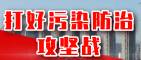本文節選自《晉劇坤伶須生開宗泰斗丁果仙》之《品評》卷,由北岳文藝出版社授權發布
丁果仙,小名果果,唱戲成名后,群眾特贈藝名曰:果子紅(中路梆子稱須生為紅)。她是本劇種出類拔萃別開生面的演唱家,唱做俱佳,而對唱腔的貢獻尤大。“丁果仙”三字,乃譽滿三晉之雅號。
1949年太原解放之初,她在太原天地壇一處四合頭的小院子里居住,房中掛著“須生大王”的鏡框,還貼著壽陽某老先生書贈的條幅,上寫“忽聞三晉馬連良,竟爾登程到壽陽,……”等詩句,足見丁果仙在解放前就已在廣大群眾中形成“須生大王”之影響。全國解放以來,她演出過許多拿手戲,卻未能有人及時地收集研究、整理記錄她的藝術資料。直至60年代,才有人開始注意這方面的工作,曾收集過部分資料,又因極“左”思潮的干擾,繼之以十年動亂,丁果仙慘遭折磨,彼此都在劫難逃,自顧不暇,只能將資料工作停了下來。
她是全國著名的表演藝術家,1952年全國第一次戲曲觀摩演出大會中,榮獲表演藝術一等獎。現在整理她的藝術生活,應對她的身世和成長過程、別具一格的藝術特色,進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她的成長和藝術創作道路,和整個中路梆子的繁榮發展分不開;其辛勤學藝的倔強性格,和她的出身歷史有關;其表演藝術特色之形成,和全國解放以來思想覺悟的提高分不開。只惜過去記錄下來的資料,十年動亂中全部散失,如此其人,竟遭終天之恨,令吾欲見無緣。時乎不能再來,只能從個人點滴記憶與向老者查訪所得,來進行簡略的探索。
一、丁果仙的身世
丁果仙的家世,極其可悲,問起她的生身父母是誰,不知道!其父母被窮困所逼,把她自小就賣給丁家,約從四歲上開始,再未享受嚴父慈母之愛。憑記憶只知是河北束鹿縣人,何區?何鄉?何街?何巷?一無所知。她的姓氏,只有姓錢的模糊印象,亦難肯定,賣給丁家,只能姓丁。據省晉劇院《院刊》1982年7月第一期所載《藝術巨匠丁果仙》一文中云:“1909年,丁果仙生在河北省束鹿縣一個姓錢的貧苦農家里,三歲上爸爸因病去世,四歲上媽媽為了全家活命,將她賣給山西太原丁鳳章做養女,從此改名丁步云,小名果果……”這就是她的身世。從幼兒時起,就離開親生父母,過著寄居生活,缺衣少食,啼饑號寒……
二、學戲與賣唱
約在光緒二十年(1894)前后,蒲籍著名老藝人紅菊花,在清源縣杜村創辦的兩期科班中,即有學員乳名毛旦者,晉中人,工須生,出科后起名孫竹林,長年在晉中、太原一帶搭班唱戲。當丁氏姐妹長到七八歲時,孫竹林每當冬天散班后,接受丁鳳章的邀請,到丁家居住,給丁氏姐妹教戲(義姐是丁巧云,亦為丁家收養的孤女),她們后來成為本劇種在山西的第一代女演員。果果學唱須生,巧云學唱青衣,她們的開蒙戲是《殺府》《賜環》《采桑》《走雪山》等。學過一冬之后,小姐妹能夠清唱些戲。但是一過了年,孫竹林出去搭班,家里又無人教戲,也不能堅持練唱。此時為民國五年(1916),適有蒲籍生角老藝人名順保者,在奶生堂開辦了第一個女科班。丁鳳章即送巧云、果果前去隨班學習。當時政府禁止女娃子學戲,又因女科班在清源大常村唱過一臺戲后,遇時瘟流行,死傷百余兒童,傳言女戲班沖撞神靈,惹禍遭災。從此女戲班賣不出臺口,只好流落在泰山廟賣唱。按照丁鳳章的意圖,一則試探觀眾對她們是否歡迎;再則讓她們向觀眾要點錢,養家糊口。當時巧云嗓子不太好,唱后收錢較少;果果嗓音很好,唱后還很能收點錢。每年一到冬天,老順保和孫竹林即到丁家,教小姐妹們唱戲。小姐妹在泰山廟賣唱度日,共度過三個年頭。
當時南方各劇種,已出了不少女演員,本劇種在張家口一帶,也有大女子、二女子、大牛牛、二牛牛們登臺露演,稱為坤角,唱得很紅,賺錢很多。丁鳳章心想,如能在山西培養出兩個坤角來,走班子能賺大錢,孩子們一輩子有辦法生活,我二老晚年也有依靠。據丁果仙自己講:“我們在前院學戲,后院就是妓女院,老人要我們加緊練功(如唱功、頂功、腰功、腿功等),一早一晚必須狠狠地練;另一方面,還讓我們加緊纏足。當時自己才十歲左右,也感到自己沒有親生父母,只得靠自己努力,尋找謀生之路。盡最大的努力,爭取走唱戲這一條路,靠藝吃飯。但是也得從壞處著想,萬一學戲不成,還得做當妓女的準備。”所以到后來是自覺地在練功上努最大的力。另外還繼續纏足,足趾被縛,血脈不能流通,三九寒天,冰雪在地,破鞋爛襪,難以御寒。凌晨在野外練功,將足趾凍爛化膿,裹足布與膿血、皮膚與肌肉凍在一起,一步一疼地練功,從未停止。冬練三九,夏練三伏,每天早早地就到了海子邊,練嗓子、拿大頂、下腰、壓腿,從不間斷。她見湖邊青蛙鼓著大肚,有起有伏地高聲叫喊,聯想到自己在練唱中,也可以運用腹中之氣,三回九轉。經過若干次的試驗,感到這樣唱出來的腔調,音純氣足,別有韻味。她那別具一格的唱腔,就是從這里開始練出來的。腰腿功夫,也是在此時練出來的。她少年時期的生活,即在如此殘酷痛苦中度過的。當時她并不熱愛戲劇,而是為生活所逼,不得不加緊學戲。倔強的性格,堅定的學戲精神,是在困難環境中千錘百煉鍛鑄出來的。從和她的親生母親離別之日起,至她搭班子唱戲之日,這是丁果仙最艱苦最困難的時期,也是成長變化轉折的關頭。從家庭轉移至泰山廟賣唱,多少人情冷暖、世態炎涼、說長道短、眉高眼低,數年來日有所見,耳有所聞,在幼小的心靈中,經過長時期的切身體會,對社會上的斗爭生活,日積月累,轉化成了相當豐富的戲劇生活素材。
她從學戲、練功、賣唱,經過艱苦的努力,把唱戲謀生之路打開了,對中路梆子的唱腔,初步掌握了要領,音色很好,音量較大,氣度有法,節奏準確,即使清唱一段,也能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同時學會了若干戲,練下了一身功夫,為搭班唱戲做好了思想意識和演出技巧上的準備。
三、在晉劇繁榮時期登臺
小姐妹離開泰山廟,開始搭班唱戲時,是民國八年(1919),丁果仙才十一歲。此時正是晉劇發展史上相當繁榮的時期。政局相對穩定,商業頗為發達,當地的中路梆子名老藝人,成批地出現在戲曲舞臺上,使劇種的特色更濃,聲譽更高。有不少知識分子、教育界和工商界人士,亦參與了中路梆子的研究改革活動。每年冬天,祁、太等地有不少熱愛戲曲的東家,邀請名藝人到家,管吃管用,研究戲曲藝術。這時期晉中各縣成立的字號班較多,如太谷楊家創建多年的錦霓園、二錦霓園;名老藝人三盞燈(郭坤)承辦的坤梨園;平遙田永富與徐溝陳鈺承領的自成園與自誠園;太谷胡萬義承辦的萬福園與小萬福園,先后在晉中一帶活動。此時蒲籍名老藝人如三盞燈、老十二紅占魁師傅、二八黑(尚云峰)等都還健在,十七生董全福風華正茂;而晉中籍的名藝人,有老三兒生孟珍卿、蓋天紅王步云、十三紅張錦云、說書紅高文翰以及毛毛旦王云山、天貴旦王春元、十四紅、桂兒紅等,人才輩出,爭芳競艷。他們按照各自的條件,發揚獨創精神,創造了不同的藝術流派。在中路梆子舞臺上,呈現出史無前例的繁榮景象。丁果仙就是在這樣一個繁榮時期開始搭班唱戲的,她跟上師傅住班子,能唱若干戲,觀眾感到新奇,初露頭角就得到好評。到20年代中期,她跟了第一個丈夫冀午齋。冀午齋大號冀鳳儀,平遙人,在晉中一帶包稅,亦有人說是稅務局長,有錢有勢,當地有一定聲望。要從年齡上講,與丁果仙相差三十余歲。據劉文才老藝人講,冀午齋是將三兒生所承的字號班錦霓園收買過來,改稱錦藝園,名角云集,聲震三晉。此時三兒生師徒、說書紅師徒、玉石娃娃(劉玉富)師徒、果子紅姐妹,都在錦藝園班內。果子紅在山西為第一代女演員,號稱坤角,頗負盛名。她丈夫又是班主,班內名老藝人都吹捧她。她即以這種特殊地位,向各位名老藝人廣泛學習,認真鉆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藝術特色,在中路梆子原有的唱腔、表演等藝術基礎上,有了新的突破。
四、博采眾長、融為一體
丁果仙的藝術才華和獨具特色的天賦條件,使她成為中路梆子中很特殊的人物。她模仿性特強,鉆研勁很大,無論唱腔或是表演,學誰像誰,惟妙惟肖。莫說在風華正茂的青年時期,接受能力特強;即使到晚年,一談到×老前輩的表演和唱腔,不論是紅、黑、生、旦、丑,說到就到,一學就像。在錦藝園唱戲時期,她創造性地演唱《花子拾金》,學的是毛毛旦姑姑、天貴旦娘娘、三兒生叔叔的《撿柴》,在老前輩的原唱腔基礎上,狠抓聲腔特色,并給以適當的藝術夸張,能使滿場觀眾為之捧腹。在老觀眾中至今仍留有很深的印象。她在新化戲院曾反串過《二進宮》中的徐延昭(大花臉),老成持重,不茍言笑;也反串過《打金枝》劇中的金枝女,裊裊娜娜,嬌氣十足。她在現代戲《小女婿》劇中,卻扮演了彩旦式的陳快腿,如此風騷的人物,放而不俗,戲中有節。在本劇種若干劇目中,她可扮演各行當角色,而且演得相當成功。
她的行當,是本劇種的正工須生,且有“大王”之稱。她對前輩須生蓋天紅與十三紅兩種不同流派的唱腔,一一進行認真學習,在演出劇目中,根據人物性格發展的需要,創造出自己獨特的唱腔。她從說書紅的念白與表演中繼承了許多優秀的藝術成果,如《詳狀》中大段說白與耍茶碗等表演技藝,把姚達這個人物,表演得很活,惟妙傳神,極為感人。再如《賣畫劈門》中的一段夾板唱段,《蝴蝶杯·訓子》一折中的介板唱腔,《八件衣》行路中的流水唱腔,《走雪山》劇中的介板對唱等,都是她在繼承前輩傳統唱腔的基礎上,大膽地進行了革新創造,并由自己設計出能夠表達各種不同感情的唱腔。所以她在中路梆子的藝術發展道路上,既是忠實的繼承者,又是革新創造的能手。我們在聽唱中反復捉摸,感到她的一些唱腔,既像某某老藝人的唱腔,而又不完全相同;有的唱腔,明顯地感到是她的革新創造,而又合乎本劇種的音樂旋律,成了更優美更好聽的中路梆子唱腔。她的唱腔,推動了整個劇種聲腔的發展提高,“出類拔萃的表演藝術家”這樣的評價,從當前本劇種來說,只有丁果仙是當之無愧的。
客觀地講,丁果仙于20年代出現在中路梆子舞臺上,可謂適逢其時。之前已有大批名老藝人,在繼承革新傳統藝術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丁果仙在此基礎上,進行了集中概括、加工提煉,將本劇種的唱腔及整個表演藝術,提高到新的水平,起到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巨大作用。接著有大批女演員相繼出世,使中路梆子藝術發展到現在的水平。任何天才的藝術家,只能在一定的時代,一定的客觀形勢下工作生活,方可起到不同凡響的具體作用,絕不會超脫自己所處的時代和客觀現實而出人頭地。我們應當承認前輩藝人遺留下來極其寶貴的藝術遺產,更要肯定丁果仙對本劇種繼承革新的重大成果,她是百花叢中的一株更為鮮艷的花朵,推動了晉劇藝術的發展與提高。
(本文全文共分為十一個篇章,刊載于《晉劇坤伶須生開宗泰斗丁果仙》之 《影行》卷第一章“評不完的果子紅”;原載《山右戲曲雜記》1991年11月)